空军为何会被神话?从一战德法空军待遇,了解神话英雄背后的原因
- 游戏资讯
- 发布时间:2025-01-16 14:56: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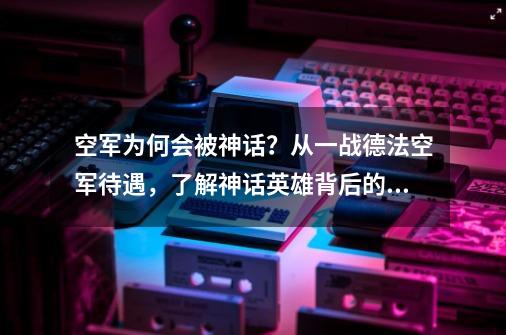 第17章 空 战
第17章 空 战
第17章 空 战
第17章 空 战
在战斗机飞行员的字典里,永远没有“战后”这个词。
——劳尔·吕夫贝里,拉法叶中队
他们是这场战争中的骑士,无所畏惧亦无可挑剔,他们再现了骑士精神的时代,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勇敢无畏,更因为他们的精神高尚圣洁。
——大卫·劳合·乔治
于下议院
1917年10月29日
重炮兵在怨气冲天的步兵眼里也许是遥不可及的存在,但还有一小群人比重炮兵看起来更加遥不可及,简直像是属于另一个世界。5月,雷蒙·朱贝尔在炮火纷飞的死人山地狱里抬眼望天,稍带嫉妒地注视着纳瓦尔(Navarre)驾驶的一架猩红色飞机在法军阵地上空上下翻飞,做出各种特技动作,炫耀着自己的又一次空战胜利。他想到,这些“快乐的飞行员在空中格斗中无论胜败,都能享受到那些卑微到尘土里、默默死去的地面士兵们的欢呼喝彩。他们是这场战争中唯一一群能按照自己梦想的方式生活,甚至按照梦想的方式死去的人”。虽然飞行员的平均寿命实际上比机枪手短得多,但考虑到地面上无穷无尽的折磨以及残杀,步兵们还是更嫉妒飞行员。飞行员的死亡常常意味着被活活烧死,但起码死亡来得猝不及防、干净利落—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步兵们对飞行员的羡慕嫉妒常常伴随着自卑。在头顶盘旋的飞机,还有它们保护的系留炮兵观测气球,都让步兵们感觉自己像是地上的啮齿类动物,无遮无拦地暴露在具有朱庇特大神一般破坏力的神鹰洞察一切的目光之下。飞行员们听不到下面战斗的喧嚣,事不关己地观察着地面微小的火光—仿佛那是镜面反射的光,还有那些腾起的烟雾。这一切都是如此遥远,根本无法让他们联想起地面士兵所经受的种种苦难。这里首要的原因是凡尔登战场本身就狭小得可笑,即便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原始的飞行器所能达到的高度,飞行员也能将敌我双方一览无余,可以同时看到自己的远程大炮和敌人后方的被炮击目标。夜间巡逻的飞机有时候能同时看见自己的基地和敌人的机场,它们的灯火在远处若隐若现,就好像大地撒上了磷火一样。飞行员在俯视战场的时候,常常会油然升起一种混杂着厌恶感的傲慢情绪,就像是一名个人主义者看待群氓的那种轻蔑。有一位空中观察员伯纳德·拉丰(Bernard Lafont)感叹道:“不加反抗地接受如此悲惨的生活状况,这是多么怯懦可鄙的一件事啊!这简直是怯懦到了极点。”
飞行员还有另一个理由让他们自觉高人一等,可怜的普通士兵每天津贴只有5个苏,而法国空军当中区区一个下士每天的额外飞行津贴就有2法郎,军官则有10法郎。此外,战斗机飞行员每击落一架敌机可以得到3天休假,还能在绶带上添加一枚棕榈叶装饰。法国轮胎制造公司米其林还建立了一笔基金,给予击落敌机的飞行员以大笔奖金。法国第一号空中王牌①居内梅(Guynemer)在死前积攒了差不多15,000法郎的奖金(他把这笔钱捐赠给了伤残飞行员救济组织)。最重要的是,这场枯燥战争中的无名之辈太多了,公众急需造星追星,而空中王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得到的崇拜,远多于1940年不列颠空战中那“一小群人”(The Few)所受到的追捧。审查制度对新闻界施加的限制太多,于是媒体把空战英雄几乎包装成了漫画里的超级英雄,每天喋喋不休地描述并且夸大他们最新的冒险故事,对他们漂亮的制服发表些大惊小怪的评论。著名的女演员会给素不相识的王牌飞行员写信,诚邀对方下次度假的时候来巴黎和自己共度美好时光,还有数不清的颂歌和崇拜信如雪片般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德国的奥斯瓦尔德·波尔克平均每天会收到23封此类信件)。德国第一位伟大的空中王牌马克斯·殷麦曼(Max Immelmann)阵亡之后,德国皇太子偕20位将军出席了葬礼。而居内梅在身后几乎被神化了。他于某一天驾机飞进了云层,从此杳无音讯,没有人发现过他的尸体或者座机的残骸,此后整整一代法国小学生都在传说他的肉身已经进入了天堂。有些王牌飞行员觉得这种程度的神化令人厌恶,低调的波尔克在休假期间去听歌剧时就遇到过这种尴尬,剧中特意插进了一段歌颂他的咏叹调,结果波尔克在这段歌曲结束之后从歌剧院偷偷溜了出来。
公众如此追捧飞行员,无疑是因为这个职业人数稀少,他们的武器又是如此新奇。法国参谋学院院长在1910年宣称“飞行是一项很好的运动,但对陆军来说百无一用”,他的评价代表了当时军界的正统观念。法国在开战时拥有的飞机不到150架,德国的飞机也只稍多一点点,但在开战第一个月,加利埃尼运用飞机侦察到克鲁克在马恩河战役中所犯下的经典错误,这次事件彻底否定了那位院长的观点。一直到战争结束时,法军都在竭尽全力扩充空中力量,但飞行员总人数仍然不足13,000。(为了对空中王牌的生还概率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我们可以把这个总数跟以下数字对比:3500人阵亡,2000人在训练事故中身亡,另有3000人在飞行事故中受伤。)法国的工业组织混乱,没能及时转入战时轨道,等到工厂终于开足马力为军队生产飞机以后,却又犯了另一项错误:生产的飞机型号过于庞杂—德国人没有犯类似的错误。第一批法国战斗机飞行员的座驾是布莱里奥式(Blériots)战机,巡航速度每小时50英里,爬升到6000英尺要花一个半小时。法军后来又列装了法曼式(Farmans)战斗机,这种战机很快得了个“鸡笼”的绰号。法军还有考尔德隆式(Caudrons)战机,当时一名法国飞行员说拿它跟德国当时的主力战斗机相比,就像拿卡车跟劳斯莱斯轿车相比。居内梅曾说如果德国人飞的是法国战斗机,他能保证每天打下来一架。直到1916年春天法军装备了时速107英里的纽波特式(Nieuport)战斗机并让其在凡尔登战场亮相以后,法国飞行员才总算拥有了能和德国人相抗衡的装备。但德国人自己也没什么可以得意的,他们在战争初期也犯了一个大错,就是集中资源生产齐柏林式飞艇,德国人在战争大部分时间里都能对盟军保持技术优势,几乎全赖一个25岁荷兰人的才智,他就是托尼·福克尔(Tony Fokker)。
当时双方战机的武器和装备都同样原始,无线电通信手段还没有被发明,炮兵校射飞机跟地面联络主要依靠把情报(一般是在地图上做标记)装进盒子里用长飘带扔下。而地面部队则用在地面铺设标记,或者用6英尺长的白色帆布在地面组字母的方式来向飞行员传递消息。这种办法在凡尔登当然会招致敌军炮火的猛烈袭击,所以行不通。莱特兄弟的这项发明刚被改装用作空战的时候,飞行员要么在空中互掷飞镖,要么用佩戴的手枪向对方射击。后来飞行员用上了步枪乃至机关枪,福克尔在1915年发明了一种同步器,让机枪能在螺旋桨叶片的间隙中射击,这也许是整个空战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突破。法国人在这方面也落后于德国人。法军的机枪有缺陷,关键时候总是卡壳,飞机降落时又经常不经击发自动开火,把自己的地勤人员打死,这让法国的空中王牌们大为光火。德军的航空机枪不需要重新装弹一次可以发射1000发子弹,法军机枪的弹夹只能容纳57发子弹。如果想在空中换弹夹,飞行员就要从座舱内探出身子半爬出来,同时用双膝夹住操纵杆维持飞行状态,这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技巧,同时还得留心敌人的战斗机是否就在附近盘旋伺机围猎。
但法国早期的空战战术比德国人的优越得多,因为这类单打独斗的战争形式特别对得上法国人个人主义的脾气(尽管后来,法国飞行员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曾有一名法国飞行员说道:“我们都是些避难者,躲避对自由精神的禁锢,躲避军队严格的纪律……”自从中世纪长弓发明以来,欧洲战场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单挑的场面。当双方的王牌在空中相遇,于云端之间展开令人目眩神迷的格斗,战争中的其他一切都被遗忘了,战壕里的士兵停下来观赏空中格斗,就像希腊和特洛伊双方大军静观赫克托耳跟阿喀琉斯决战一样。在这类高度个人主义的战斗当中,飞行员们又复活了全民战争时代来临后就早已消失的骑士气概和运动家精神。敌对双方之间培养出了惺惺相惜的同志情谊。有一名德国飞行员曾在空袭法军基地的时候,不小心丢下了一只昂贵的皮手套,第二天他飞回法军基地上空把另一只手套也扔了下去,还附上一张纸条,请求捡到手套的人把它留下,因为他自己反正留着单只手套也没什么用。而捡到纸条跟手套的法国飞行员也很有中世纪的骑士风度,他飞到德军基地上空扔下一封感谢信。像冯·里希特霍芬(von Richthofen)这样的冷血杀手王牌很少,大多数飞行员都如同波尔克或者纳瓦尔一般憎恶杀戮,每次击落敌机都尽可能瞄准敌机的引擎而不是飞行员射击。如果敌方某位著名王牌阵亡了,胜利阵营当中更多表现出来的是惋惜和哀悼,而不是喜气洋洋:波尔克本人阵亡后(他和自己最好的朋友空中相撞),位于航程范围之内的每一个英军基地都派出飞机去波尔克所在基地上空投下花圈,根本不顾被击落的危险。虽然这种骑士精神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一直延续,但凡尔登战役标志着单打独斗的空中王牌时代的结束。直到凡尔登战役,“空中力量”( Airforce)这个词才第一次具有了真正的意义。
霞飞和德·卡斯特尔诺曾在1916年1月向普恩加莱总统信誓旦旦地保证法国在空战领域对德国保有优势。可是凡尔登战役开始时,法国空中力量却在德军面前居于绝对劣势,单从数量上说就是接近1比5的劣势。法军步兵垂头丧气地看着满天的德国福克尔式飞机在战场上空任意翱翔,精确地指引着德军的火炮射击。不过法国空中力量的反应也很快,其负责人巴雷斯(Barés)上校在空中战略方面颇具慧眼,立即在巴勒迪克建立起自己的前线指挥所,一周之内就把当时法军总共15个战斗机中队当中的6个部署到了凡尔登地区,尽管当时陆军仍然对飞机这种新式武器的效能持怀疑态度,不太愿意合作,甚至没法给他提供地图和飞行员宿舍里铺床的稻草垫子。法军在凡尔登除了有6个战斗机中队以外还有8个侦察中队,总共120架飞机。巴雷斯令人信服地展示了空军的机动部署能力。这支庞大空中力量的指挥官只是一名少校—德·罗斯(de Rose)侯爵。他从巴雷斯那里受领的任务很简单—“扫清天空”。这位侯爵当时40岁,曾在骑兵服役,斯皮尔斯描述他具有“昂扬和英雄的精神”,他穿的军装似乎也是自己设计的。他虽然在5月一次飞行事故中身亡,但当时几乎已经完成了扫清天空的使命。
德·罗斯首先着手调集了60名最顶尖的飞行员,这个阵容明星荟萃,几乎集齐了当时法国所有著名的空中英雄,其中很多人聚在一起组建了著名的“飞鹳中队”(Groupe des Cigognes)。那几年里,这些少年英雄们生气勃勃的脸庞让人们看到了未来(他们中绝大多数才二十出头),他们是如此机警而敏锐,总是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这与前线大兵拉碴的胡子,与他们军官那气冲斗牛的上翘唇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队长布罗卡(Brocard)上尉刚到凡尔登不久就在空战中受伤,第二年去职,因为他很难把旧时单打独斗的空战模式跟凡尔登地区空战的新情况相适应,而飞鹳中队的盛名就来自这种旧式单打一的空战模式。坚强到令人拍案称奇的夏尔·南杰瑟(Charles Nungesser)中尉也是这个中队的成员,他在战前曾是拳击手,在凡尔登战役时,因重伤在身,只能让人抬进飞机座舱,而且只能用一只脚来控制方向舵。可他的飞行技巧娴熟,有一名拉法叶中队的美国飞行员甚至说,南杰瑟的飞机仿佛不是由他的身体操纵的,而是受到他的思想控制似的。他仅在凡尔登地区作战期间就打下6架德国飞机外加1个观测气球。南杰瑟的下巴是人造的,由黄金制成的骨架固定在一起,他笑起来的时候嘴会歪着,并露出整整两排大金牙。他虽然重伤在身,但在战斗和娱乐时都同样地奋不顾身,常常在一整天的战斗之后,开着自己那部巨大的敞篷跑车长途奔袭150英里去巴黎花天酒地,狂欢滥饮一夜后再开回基地,升空参加清晨巡航。他在空战中17次受伤,却是少有的能活到战后的空战王牌。中队里另一位明星是英俊的20岁准尉让·纳瓦尔,他在杜奥蒙堡陷落第二天就取得了飞鹳中队的第一个击坠战绩。他父亲是有钱的纸制品制造商,某种程度上他算是个花花公子,厌恶杀戮,声称自己只是被迫进行空战。空军内部的纪律已经够宽松了,纳瓦尔还是拒绝服从,根本不好好写航空日志,还曾因不服从命令被关过禁闭。前线战壕里的官兵特别喜欢他,因为只要空中没有敌人,纳瓦尔就会驾驶着自己那架红色飞机在前线上下翻飞,表演令人心悸的空中杂技,而这是被严格禁止的(冯·里希特霍芬把座机涂成红色还是拾他的牙慧)。纳瓦尔在凡尔登进行过257次空中格斗,大多数时候都是以寡敌众,打下了11架敌机。受伤后,他待在医院里,脾气极其暴躁,在康复疗养期间更是以放荡的丑行震动了巴黎。兄弟阵亡给他精神上带来很大打击,让他陷入长期的抑郁情绪,最后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住进了疯人院。1919年,纳瓦尔演练从凯旋门下穿越的飞行特技时,撞上电话线死于非命,有证据显示他有可能是自杀的。
所有这些明星中,最耀眼的那颗无疑是居内梅(Guynemer)。他当时21岁,在飞鹳中队调到凡尔登时刚刚成为军官,1915年夏天的一个早晨,还是一名下士的居内梅打下了3架敌机,那是他第一次出名。居内梅家族的英勇事迹可以追溯到查理曼大帝时代,他本人却没有英雄人物那种孔武的相貌。他很瘦削也很清秀,有点女性气质,因为身体弱曾三次报名参军被拒。他和所有参谋军官一样注重外表的自我修饰,身上总是挂着全部的勋章。德里昂中校在战前写过关于潜艇战和空中飞船的假想战争小说,居内梅少年时代被这些书深深地吸引了,所以把战争和飞行都作为自己狂热的志趣所在。他回后方休假期间,每次都有大把的名媛美女想要和他上床,他却无动于衷,宁愿把时间花在跟飞机设计师讨论技术细节上面。他对自己的3架飞机了如指掌,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检查引擎和机枪。他曾说:“飞机对我来说就是飞行的机关枪。”他也的确是个空中神枪手,这是他能活得这么久的秘密,尽管居内梅不像那些活到战后的王牌—比如勒内·丰克(René Fonck)、纳瓦尔或者南杰瑟—那么头脑冷静,或者飞行技巧娴熟。居内梅高度神经质,每次都像一根压紧了的弹簧突然被松开那样冲进战场,奋不顾身地扑向对手,这种冲动让很多初出茅庐的飞行员丧了命。每次救他命的都是他那高度精准的射击术。居内梅的传记作者亨利·波尔多(Henry Bordeaux)说,他在降落之后仍然处在神志不清的状态当中,“就像被周身流转的电流电到了一样”。他经过无数次空中格斗,每次都极其幸运。这种神经质本来可以要了他的命,在凡尔登战场上也的确有一次差点真要了他的命。当时他跟飞鹳中队的战友们一起编队飞向前线,打下自己的第8架德国战机。其后,3月13日,两架德军战斗机夹攻居内梅,在10码距离内向他开火,两颗子弹击中左臂,无数金属碎片打在他脸上,其中一块打进下巴的碎片后来再也没能取出来。脸上的血糊住了他的眼睛,他开始俯冲,居然成功迫降在地面,只是机身右边侧翻朝上而已,与此同时还有第三架敌机想在他迫降的时候结果他的性命。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凡尔登战场上作战。他伤还没好就在4月26日逃出医院重返战场,可是又被送回医院,就像个淘气的小孩一样。他8次受伤,最后一次在伤口还没有愈合的情况下,就重返蓝天继续战斗了。1917年9月居内梅在云端消失,法兰西举国哀悼。他总共击落54架德国飞机。
1916年2月,德国人在凡尔登地区集中了当时世上最强大的空中力量,总共有168架飞机、14个“龙式”系留气球、4艘齐柏林飞艇。可是德国人犯了两个严重的战术错误,以至于根本没有意识到制空权的价值就把它拱手送给了法国。第一个错误在于德国人把空中力量都密集用于防御目的,组成所谓“空中保护网”,以确保德军防线上空的安全。德国人把凡尔登上空划分为若干个很小的空域,每个空域保证24小时都有两架飞机巡逻。因为燃料问题,每对巡逻飞机在目标空域上空的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而且只能用速度相对较慢、比较笨重的双座飞机进行这种巡逻。计算下来,以1916年飞机的速度,德国人至少需要720架飞机而不是168架,才能有效地执行封锁天空的任务。实际上,这些飞机的数量刚刚够驱逐从战斗一开始就零星飞临战场上空的寥寥几架法国侦察机。精神抖擞的飞鹳中队来到凡尔登战场以后,开始兴高采烈地随意攻击那些散布在“空中保护网”各处的德军飞机。一旦撕破这张网,法国飞机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击落“龙式”系留气球,这些气球是德军炮兵必不可少的耳目。虽然法国人的飞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如德国的,但他们在10天之内就以自己干劲十足的进攻精神从德国人那里夺得了制空权。其后,奥斯瓦尔德·波尔克来了。
波尔克的父亲是萨克森人,曾做过教士,后来当了学校校长。在来凡尔登之前,25岁的波尔克已经打下了9架敌机,是德国最高战功勋章“功勋勋章”最年轻的获得者。1916年1月底,他被秘密地从杜埃(Douai)调到凡尔登以北的雅梅斯(Jametz),加入构建“空中保护网”的行动。开战前,他因内脏疾病被强制送进医院,非常不情愿地错过了初期的作战。然而,后来他不知怎么地贿赂了看护溜出医院,击落了一架胆大妄为地扫射自己基地的法军飞机。到3月11日,德军空中指挥部对形势已经感到非常焦虑,于是授予波尔克全权,让他以任何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把空战打到法国人的后方去,尽管波尔克当时只是一名区区的中尉。波尔克立刻把自己的基地从离前线14英里的雅梅斯前移到离死人山高地6英里的默兹河畔锡夫里(Sivry-sur-Meuse),他认为雅梅斯离前线太远了。(当时飞机航程很短,因此把基地设在敌方炮火射程之内是很常见的做法。)在最初的10天内,波尔克又添了4架个人击坠战绩。法国空军开始遭受损失,仅在飞鹳中队里,就有中队长布罗卡上尉、居内梅以及其他几名顶级飞行员受伤暂时撤离了前线。德国人重获战场主动权,炮兵火力也变得更精准,为3月底在左岸地区进攻的胜利平添了助力。波尔克在4月11日阴郁地写道:“仗一天比一天难打。法国人不来进攻我们了,他们远远地在后方飞行。”
但是空中作战的攻防转换速度很快。法国开始采取集中力量编队飞行的方式,虽然编队的控制还比较松散,但这是背离旧式空中决斗模式的第一步。波尔克写道:“他们一次出动多达12架战机保护两架侦察机。我们很难突破保护幕打掉侦察机。”德国空中力量还第一次失去了数量优势。巴雷斯和德·罗斯运用优秀的组织才能在4月中旬把凡尔登地区的法国空中力量提高到226架飞机,这么大密度的兵力集中在此,法金汉那种在所有战线都保持兵力的战略根本就不能或者不愿与之抗衡。5月7日,德军部队在蒂欧蒙(Thiaumont)集结,准备发动进攻,却突然遭受由空中引导的法军精确炮火的火力急袭,德军这才气急败坏地注意到,德国战斗机第一次无力驱逐法军的侦察校射飞机。5月稍晚时候,法国战斗机装备上由某海军军官发明的特殊火箭,在一天之内就把皇太子5个珍贵的“龙式”系留气球打成了一团团火球。波尔克此时已在取得自己第18架战绩以后被提升为上尉,他挺身而出提出组建游猎中队(后来英国皇家航空队给他们起名叫“飞行马戏团”),将一组12架飞机分成4个三机编队,互相之间密切支援。但“飞行马戏团”还没来得及在凡尔登地区完成编组,6月18日就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说殷麦曼阵亡了。德国不能再损失另一位伟大的空中英雄,于是德皇亲自下令禁止波尔克飞行,并把他调往俄国前线从事训练工作,这令波尔克大为失望。
如果不是殷麦曼的阵亡,波尔克的“飞行马戏团”几乎肯定能让习惯于单打独斗的法国飞行员吃尽苦头。因为7月份索姆河战役打响后,波尔克说服了上级相信前线不能没有自己,并亲自率领“飞行马戏团”打下了51架敌机,其中20架是他的个人战绩。那年秋天,德国空中力量达到了顶峰状态,一个月之内在索姆河上空击落123架协约国飞机,自己仅仅损失27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机战术在这里诞生。与此同时,在空战战术真正的诞生地凡尔登战场,法国一直都牢牢地掌握着制空权。6月和7月是贝当的部队最接近崩溃边缘的时候,却也是德国的空中力量最为虚弱的时刻。如果德军取得制空权,凡尔登战役很可能会是另一个结果。法国空军在凡尔登取得了大胜,但他们付出的努力代价太大。在凡尔登战役之后,法国空军一直在走下坡路,空中战役渐渐成为英德两国之间的争斗。
德军在凡尔登的空中作战中所犯的第二个错误是,他们没能利用初期的优势切断法国通往凡尔登的补给线,这个错误比第一个的严重得多。当时轰炸已经是一种成熟的作战形式(早在1914年9月,德国陶伯式飞机就轰炸过巴黎),德国人当时的确拥有轰炸所需的飞机。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德国人当时没进行轰炸,让凡尔登的法军逃过一劫,似乎同时代的德国评论家们也同样不理解。战后不久,汉斯·里特尔(Hans Ritter)评论说:
这条交通动脉(指“圣路”)拥挤异常,已经达到通行能力的极限,如果对其进行精心组织并不断重复的空中轰炸,那么能在多大程度上削弱这条动脉是不言而喻的。第一次轰炸后,就会有数不清的被炸毁、正在燃烧的车辆堵塞道路。到处爆炸的弹药车会加剧混乱。重型炸弹造成的弹坑会在多点切断公路。那里必然会出现无法疏通的乱象。
他继续指出,德国当时有3个中队总共72架重型C式飞机正在待命,只需半个小时便能飞临目标上空,每架可以投下一枚200磅炸弹。所以德军每天可以向圣路投下20吨炸弹,这还没算上打击敌方士气的夜间轰炸。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德军把这些飞机浪费在攻击铁路枢纽上,而铁路枢纽本来就已经在德军远程炮火的有效覆盖之下了。此外皇太子集团军还能动用7艘齐柏林飞艇进行远程轰炸,其中包括一艘德国最大最新的LZ95号飞艇,它能够爬升到12,000英尺高空,没有任何战斗机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可是直到6月,德军才开始全力轰炸巴勒迪克等至关重要的交通枢纽。另一位德国军事评论家赫尔曼·温特指出,德军没有试图对默兹河上重要的桥梁进行攻击。整个战役期间默兹河上的34座大桥只被摧毁了一座,这还是因为法军自己在2月28日错误地引爆了埋在桥上的炸药包。
德军为什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也许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答案来自德国空军参谋长霍普纳(Hoeppner)将军本人,他令人惊讶地坦陈:“我们在凡尔登并不懂航空作战的本质和精髓。”
1916年5月18日,在阿尔萨斯战区一段平静的战线上空,一架德国侦察机执行完任务后正在返航途中。然而,当它刚刚跨越战线回到自己一方,有一架战斗机突然从太阳方向向它俯冲而来。对方机翼上涂着三色旗圆形机徽,机身上却有一个之前从没见过的标志,那是一个穿戴全副羽饰的印第安部落勇士的头像。德国飞机的观察员/机枪手连忙从座舱里站起来操作机枪自卫,但在几秒钟之内,德军飞行员和机枪手都被打死,飞机也转着圈坠毁在地面。
这场空战原本可能只是官方公文里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但获得胜利的飞行员的国籍却值得大做文章:这名下士叫基芬·洛克维尔(Kiffin Rockwell),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市。洛克维尔的胜利是新组建的第124中队的第一个击坠战绩,这个中队又被称为“美国中队”,后来华盛顿的孤立主义游说团体施加了政治压力,这个中队才改名为“拉法叶中队”。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诺曼·普林斯(Norman Prince)最先提出组建这个中队的主张。他于1914年在马萨诸塞州学会飞行,然后来法国想要组建一支由美国志愿人员组成的飞行小队。他在巴黎得到一名有影响力的美国医生埃德蒙·L.格罗斯(Edmund L. Gros)的帮助,格罗斯曾参与创建了美国志愿野战救护队(American Ambulance Field Service)。这两人想尽办法找关系,从外籍军团和志愿野战救护队里拉来合适的人选,但法国当局起初不太愿意合作,直到一年以后才意识到这样一支志愿部队潜在的巨大宣传价值。拉法叶中队官方的成军日期是1916年4月16日,最初的成员是7名美国飞行员,全都是士官,指挥官是两名法国军官—泰诺(Thenault)上尉和德·拉热·德·缪克斯(de Laage de Meux)中尉。拉法叶中队装备新的快速纽波特式战斗机,最初的任务是为以孚日山脉吕克瑟伊(Luxeuil)为基地的法国轰炸机群护航。
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拉法叶中队里的美国志愿兵都是形形色色各色人等都有:有穷的也有富的,有花花公子也有大学生,有职业飞行员也有雇佣兵。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或许就是自当年拉法叶侯爵远渡重洋来美国帮助乔治·华盛顿手下艰苦奋战的大陆军以来,法国就对美国的年轻人施加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影响力。最初的7名成员在加入中队之前大多数就已经在法国作战了。威廉·陶(William Thaw)是中队里第一个被授任为军官的,当年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就拥有私人水上飞机,所以早就在法军中当上了轰炸机飞行员。陶据说是世界上第一名驾机从桥下穿过的飞行员,他的外表、身材和酗酒习惯都很像海明威。他受过一次伤,从此胳膊只能弯曲着,伸不直,但这反而让整个中队坚毅的形象更为深入人心。维克托·查普曼(Victor Chapman)毕业于哈佛大学,战争爆发时在巴黎的艺术学校学习,他马上投笔从戎,加入法国外籍军团成为一名列兵。21岁的基芬·洛克维尔是来自北卡罗来纳的医学生,也在战争爆发后加入了法国外籍军团,他和查普曼两个人的祖父都曾是美国内战时期南方军的军官。查普曼和洛克维尔在前线战壕里打过一年仗,1915年5月,洛克维尔大腿受了重伤。詹姆斯·麦康奈尔也是南方人,他和艾利奥特·考丁(Elliot Cowdin)都来自美国志愿野战救护队。伯特·豪尔(Bert Hall)是个真正的德州雇佣兵,战前就有丰富的飞行经验。他在1912年和阿卜杜·哈米德(Abdul Hamid)苏丹签了个人协议,用自己的飞机“自由长矛”(free-lance)替苏丹服务,跟保加利亚人作战,不过他很聪明,在协议里坚持要雇主每天用黄金结账。苏丹的赏金很快就告罄了。豪尔在1914年加入法国外籍军团,后来又转入法国空军,他通过迫使敌机迫降在法军战线后方,成为第一名完整缴获一架德军飞机的飞行员。
后来加入的成员当中,有个人的姓跟豪尔相同,名叫詹姆斯·豪尔(James Hall),于开战后加入了基钦纳的第一批10万人英国陆军。詹姆斯·豪尔在拉法叶中队里以运气超好著称,有一次一发高射炮弹在击中他飞机的引擎后居然没有爆炸,而是嵌在了里面。他和查尔斯·诺德霍夫(Charles Nordhoff)是形影不离的伙伴,诺德霍夫后来在中队里搞了一次“赏金兵变”。劳尔·吕夫贝里(Raoul Lufbery)在拉法叶中队成军之后几天加入,他和伯特·豪尔一样在战前就已经是职业飞行员了。他在法国出生,父母移民去了美国。1912年,吕夫贝里和一名胆大妄为的法国飞行家马克·普尔普(Marc Pourpe)组队,用一架老式的布莱里奥飞机在远东和近东地区开展了两年的巡回表演,有一次,他在中国的农村迫降,差点被迷信的当地农民打死。1914年,普尔普回国参加法军,在战争初期的空战中殉国。吕夫贝里从此心心念念要为好友报仇雪恨,最后在1918年5月阵亡,他将成为美国第一名空战王牌飞行员。
这些志愿飞行员们,此前一年要么作为外籍军团士兵在堑壕里苦战,要么待在生活条件艰苦的救护队里,在刚到达孚日山脉中野性而美丽的吕克瑟伊时,都觉得生活美好得就像做梦一样。他们的驻地是一座豪华别墅,旁边有罗马浴场。他们还能和军官一起在城里最好的宾馆用餐(这背离了法国陆军官兵分开用餐的传统)。中队最初7名成员里有4人没能活到战后,其中之一詹姆斯·麦康奈尔有点未卜先知地写道:
我想到自己拥有的豪华生活——舒适的床铺、洗浴设施、汽车,于是回想起这样一个古老习俗,古时候在献祭一个人之前都会给他提供国王般的舒适生活,直到祭祀的那一天到来。
但没有人把这种思绪宣之于口,部队士气很高昂,出击作战之余的日子也很忙,很少有机会坐下来静静地思考。飞行员们全神贯注地不停玩扑克、打桥牌,背景中一架留声机一遍遍地反复播放着毫无新意的《谁为里普·凡·文克太太付了租金?》(Who Paid the Rent for Mrs. Rip Van Winkle?)。中队的吉祥物—一只名叫威士忌的幼狮—则会亲昵地在周围安静地逡巡。中队在开派对狂欢的时候往往把当地旅馆搞得乱七八糟,让上了年岁的法国飞行员们既惊讶又羡慕。
基芬·洛克维尔取得拉法叶中队第一架击坠战绩的那天,他们接到命令转场开赴凡尔登前线,在那里拉法叶中队将面临第一次严峻的考验。5月24日,陶在杜奥蒙堡上空遭遇一场苦战,他先打下一架福克尔飞机,傍晚再次飞临战场,却遭到三架敌机围攻。他的座机弹孔累累,胳膊动脉也被一发子弹打穿,但他终究还是安全地停降到法军前线后方。他因功成为第一位获得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的美国人。伯特·豪尔也在同一天击落一架敌机,自己也受了伤。中队的伤亡越来越多,6月17日,也就是殷麦曼阵亡前一天,查普曼遭遇了伟大的德军王牌波尔克,座机遭到重创,右副翼控制装置被打坏,自己头部受伤,可是他仍然用手拉着副翼控制索的残端成功迫降。第二天,新来的飞行员克莱德·巴尔斯利大腿被一颗爆炸子弹击中,伤势严重,子弹的碎片在他的肚肠上穿了十多个小孔。法军前线部队将他从座机里救了出来,并送到后方医院,后来查普曼在一所肮脏的法军医院找到了高烧不退、口渴难耐的巴尔斯利。巴尔斯利在昏迷中喃喃呓语想吃橙子,然而1916年的法国和“二战”期间的英国一样很难找到橙子。查普曼听说巴尔斯利命不久长,于是在整个法国为他搜寻橙子,终于在6月23日找到一些,便开着飞机给医院里的巴尔斯利送去,却在途中遭到5架德军飞机的围攻。
维克托·查普曼是拉法叶中队第一名牺牲的飞行员,也可能是最受人爱戴的一员,他死后,中队里弥漫着复仇的情绪,飞行员们在空中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急切地寻找空战的机会。不可避免的事情终归会发生。洛克维尔给弟弟写信说:“我和普林斯明天要飞10个小时,尽力替维克托杀一两名德国鬼子。”两人第二天都如愿以偿击落了德军飞机,可是再次日,洛克维尔也被击落,几天以后,拉法叶中队的创始人诺曼·普林斯为了给洛克维尔报仇,飞的时间过长,返航时间太晚,在夜色中降落时撞上高压电线阵亡了。
美国在1917年参战,之后很久,拉法叶中队还在法军编成中作战。1918年2月,拉法叶中队解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队里幸存下来的每一位飞行员都被美国陆军航空队确认为由于医疗原因不适于服役!但那时拉法叶中队已经成名,他们的肩章上佩戴着两道集体嘉奖的标识,整个法军中只有居内梅的飞鹳中队享有相同的荣誉。曾在拉法叶中队作战的38名美国人当中有9人阵亡,包括7名创始成员中的4人,另有很多人受伤。中队在成立后的头半年中,总共作战156次,取得了17次胜利,其中大多数都是在凡尔登战场取得的,中队从5月到9月一直在凡尔登作战。拉法叶中队当时还没有完全成熟,就已经为凡尔登战役做出了重大贡献,更重要的是它的存在为法国的战争努力做出的间接贡献。从它作为第一个完全由美国人组成的战斗部队参战的那一刻起,拉法叶中队就成了美国公众关注的焦点,新闻媒体对它的报道与其他有关战争的报道相比也自然多得不成比例。中队成员写的家信到处流传,经常被登在当地报纸上。美国国内的公众从开战以来第一次觉得西线的这次伟大地面会战跟自己有着切身的联系。美国公众通过拉法叶中队的事迹,尤其是凡尔登战役中维克托·查普曼的英雄事迹,开始对法军官兵感到关心和同情,这是其他西线战役做不到的。凡尔登就像1940年的不列颠之战一样攫住了美国公众的想象力,相比之下,他们对索姆河的巨型会战兴趣不大。美国于1917年4月最终参战,这当然跟德国潜艇战带来的威胁有关,但法军在凡尔登的坚决作战也是不容忽视的情感上的因素。
①起初飞行员击坠战绩达到5架就可以被称为王牌,后来这个标准被提高到10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