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特辑" |美术史中的“cp”你了解多少
- 游戏资讯
- 发布时间:2025-04-16 19:3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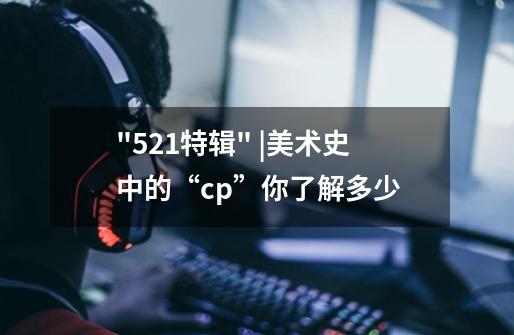
521,因为“我爱你”的谐音,成了一个温暖又浪漫的日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磕一下美术史中的cp。
伏羲女娲
第一对cp伏羲女娲当之无愧,是众多的远古氏族的图腾、符号和标志。
唐代伏羲、女娲绢画,出自新疆吐鲁番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序列中,继承燧钻木取之后的,便是流传最广、材料最多也最出名的女娲伏羲的“传奇”了:
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说文》)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淮南鸿烈·览冥训》)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太平御览》七十八卷引《风俗通》)
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禖,因置婚姻。(《绎史》引《风俗通》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近取诸身,远取于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比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易·系辞》)
伏者,别也,变也。戏者,献也,法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风俗通义·三皇》)
从“黄土作人”到“正婚姻”(开始氏族外婚制?),从“以佃以渔”到“作八卦”(巫术礼仪的抽象符号化?),这个有着近百万年时间差距的人类原始历史,都集中凝聚和停留在女娲伏羲两位身上(他们在古文献中经常同时而重迭。这也许意味着,他们两位可以代表最早期的中国远古文化?
山东武梁祠东汉画像石伏羲、女娲像
那么,“女娲”“伏羲”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物呢?他们作为远古中华文化的代表,究是什么东西呢?如果剥去后世层层人间化了的面纱,在真正远古人们的观念中,它们却是巨大的龙蛇。即使在后世流传的文献中也仍可看到这种遗迹:
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
燧人之世,…生伏羲…人首蛇身。(《帝王世纪》)女娲氏…承庖羲制度,…亦蛇身人首。(同上)
本段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西王母与东王公
汉代武梁祠东西山墙上的画像分别以身形硕大的西王母与东王公为视觉中心,并且除西王母与东王公外,其他神人和动物均被表现为侧面。这一对cp的出现明显与中国传统的阴阳观念以及“偶像崇拜”有关。
1、阴阳观念(图像内容)
孝堂山祠堂西山墙上出现的西王母,在她上方偏右的位置我们仍可发现人身蛇尾的女娲。“阴”因此由女娲和西王母同时来代表,这种现象反映出象征阴阳的图像在演变中的一个过渡状态:西王母和箕星在东汉初开始成为这种象征,但还没有完全取代传统的伏羲、女娲组合。但这一过渡并没有花很长时间,因为大多数公元1世纪的山东画像石已只见西王母而不见伏羲女娲了。
人首蛇身的西王母图像
在武梁祠东西壁山墙上表现的仙界中,东王公进一步取代了箕星而成为跟西王母配对的神祇,这代表了阴阳概念在美术表现中的更深入的阶段。这种变化不难解释:汉代的宇宙观视阴阳为对立统一的两极,任何具体事物包括男女、禽兽、天地、日月、方位等等都可视为阴阳的具体表现。对汉代人说来,阴阳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万物内在的本质。不论在理论或是艺术中,他们对阴阳相克相生“模式”的追求可以说是到了着迷的程度。对他们来说,整个宇宙之所以可以被理解,是因为阴阳对立和转化的模式是普遍的、可见的。他们把阴阳概念推而广之,运用到对所有社会和自然现象的解释中去,创造了许多具体的象征阴阳的物象,并用它们来阐发这一对概念。伏羲和女娲原本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神祇,但在汉代神话中被配成一对,东王公的创造也出于相同的动机。东汉初年,西王母与箕星被凑合在一起,刻在祠堂上作为阴阳的象征。但这样相配显然并不那么合适,因为这两个神祇并无紧密的内在联系。除了各自与东西方位对应以外,其实并没有什么理由将它们配对。因此东王公这个新神祇便应运而生了。别的不说,甚至他的名字也是完美地与西王母对应—这一点也意味着他被创造的理由。
2.宗教偶像(视觉表现)
在本部分的探讨中,焦点放到作品的构图样式以及其他有关画像风格的问题。
武梁祠西壁画像石上的东王公
武梁祠西壁画像石上的西王母
武梁祠东西山墙上的画像具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两处图画都作对称式设计,分别以身形硕大的西王母和东王公为视觉中心,再在两边配以向中心移动的神人异兽。第二,在这两幅图像中,除西王母和东王公外,其他神人和动物均被表现为侧面。
这种对称构图和正面的主神是各种宗教艺术表现神像最常见的特点。为了便于叙述,我把这种构图称作“偶像型",以与另一种我称之为“情节型的构图相区别和对照。“情节型”构图通常是非对称的,主要的人物总是被描绘成全侧面或四分之三面,而总是处于行动的状态中。这种图像一般以表现某个故事情节或生活中的状态为主题,因此可以称作是叙事性的。(以长沙出土的两幅最早人物肖像为例)与“偶像型”的画面不同,这类构图是自足和内向的,其内容的表现仅仅依赖于画面内的图像,观看这种“情节型”图像的人只是一个观者,而非参与者。
湖南长沙陈家大山出土的帛画
与以表现侧面人物为主的传统中国绘画不同,印度佛教艺术有着以对称构图表现宗教崇拜主题的悠久传统。这种构图原则是由图画主题本身所决定的,因为它的目标是要同时展现崇拜者和被崇拜者的偶像。以武梁祠为代表的偶像型构图方式来自印度佛教艺术,汉代艺术家在1世纪左右开始以这种方式表现西王母。其原因是在这个时候这位女神成为宗教崇拜的偶像,而且被等同于西方的神仙--佛陀。
本段摘自巫鸿《武梁祠》
洛神赋图
《洛神赋图》
《洛神赋图》旧传为魏晋时期的顾恺之根据曹植的同名诗篇《洛神赋》所作的人物故事手卷,此画描述了黄初四年曹植“从京域”而“归东藩”,偶遇仙女洛神,两人互传情愫后又因人神道殊,而不得不分开的无望之爱。是中国最早的爱情题材人物画。
洛神
作为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洛神赋图》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长卷的先河,也标志着中国早期绘画从政教的附属地位和礼仪的实用功能走向了审美自觉。
“盖章狂魔”乾隆帝对此画的评价是“妙入毫巅”。虽然乾隆帝的品位不如雍正高雅,但对《洛神赋图》的评价还算中肯。
惊鸿游龙
若即若离的洛神回首相望,欲言又止
顾恺之用画笔分段描绘了曹植洛水河畔的一梦,构图连贯,主要人物随着赋意,反复出现,设色浓艳,画法古拙,山石树木钩填无皴。所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系初唐以前画风。该画虽为宋人摹本,但画风仍存六朝遗韵,其原本传为顾恺之所作。
洛神赋图 局部
此外画中还出现了《洛神赋》中描绘的六龙、鲸鲵、水禽等奇珍异兽。各种传说中的神仙、树木、山水也是古拙奇特。共同营造出一个人神共处的奇幻仙境
西方美术史
吻,克里姆特,奥地利,1908年,布面油画,180×180cm,奥地利维也纳奥地利美术馆
这是一幅表现爱的抽象主题寓意的杰作。在开满鲜花的草地上,男人轻柔地抱起女人的头,富有激情地亲吻着女主人公的脸颊。男人身上的装饰都是方正色块,由黑白黄三色方块构成,象征了男人棱角分明,坚强的特质。女人身上是感性的圆形图案与流动的线条,代表了女性的柔媚和温柔圆润。女人一条手臂搂着男人的脖颈,一只手紧抓着男人的手,闭着眼睛尽情享受着幸福的感觉。她的表情是迷醉的、满足的,甚至似乎还有些害怕这幸福时刻的结束。在画面形式营造上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诸如线条和色块的组合,色彩中掺入金粉,使画面呈现出美妙温馨的梦幻场景。
暴风雨,考特,法国,1880年,油彩,木板,234.3×156.8厘米,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暴风雨》的主要欣赏点是:光线和色彩的对比和互相衬托的美感力量,这是19世纪美术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作品画面里,背景是暗的,前景是亮的;男角色彩是暗的,女角色彩是亮的。男体力量的粗旷线条,女体力量的柔细线条,在光线和色彩中得到了鲜明的对比和彼此衬托。在考特之前,也有不少取材于《达夫尼斯和克洛伊》的美术作品,大都是歌颂爱情性爱的。而考特的作品《暴风雨》抓住了达夫尼斯和克洛伊在暴风雨中逃跑的一瞬间,表达了男女不同的性感力量之美、歌颂了纯洁的爱情和自由的向往,无论是艺术境界还是艺术手段方面,与前人作品相比,都是更上一层楼。
春光,考特,法国,1873年,油画,罗斯先生收藏
在画面上,一位美丽的少女把胳膊挂在情人的脖子上,投出微笑迷人的明媚眼光,半裸地依偎着情人。她是在撒娇、还是在倾听甜美的情话?一位俊俏的小伙子,她的情人,雄健有力的双臂紧紧拉着秋千的绳索,好像是在支撑守卫着他们的爱情。小伙子略向姑娘歪着头,是在享受她的撒娇、还是在告诉她什么秘密?……春天的阳光从树丛里照过来、像舞台聚焦灯光一样照亮了美丽少女,温暖的春风轻轻地掠起了她的纱衣,饱经风霜的千年老树好像是他们的爱情见证人,每一片树叶和每一棵花草都在为他们轻轻吟唱,……看到这个盎然春机和纯美爱情的画面,就是冷酷无比的魔鬼也会酥心醉倒。
“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